
开云体育官网 李渊跪求放过10个孙子,李世民点头得意,转死后为何怒斩十孙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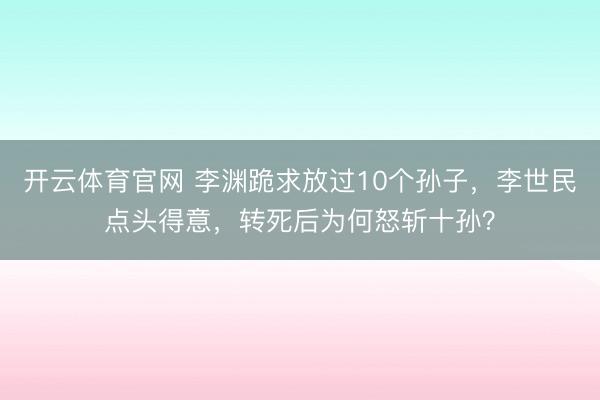
公元626年的长安城,血腥味还莫得散尽。
太极宫里,一个六十岁的老东谈主跪在我方的女儿眼前,泪流满面。这个老东谈主,是大唐的建国天子李渊。而站在他眼前的,是刚刚杀死两个兄弟、行将登基的秦王李世民。
"世民,求你了,放过他们吧。他们都是你的亲侄子,最大的不外十岁,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……"
李世民千里默良久,终于点了点头。
可谁也没预想,就在李渊回身的那一刻,十颗东谈主头落了地。
那整夜,通盘皇宫都听到了老天子肝胆俱裂的哭声。而新君李世民,在血泊中站了整整整夜,一言不发。
这究竟是如何的一场东谈主伦惨事?阿谁招待父亲的李世民,为何旋即之间就违约而肥?这背后,又瞒哄着如何不为东谈主知的奥妙?
让咱们把时间往回拨小数,回到阿谁窜改大唐气运的日子。
伸开剩余90%武德九年六月初四,天还没亮,玄武门外依然杀声震天。
李世民带着尉迟恭、长孙无忌等挚友,埋伏在玄武门内。当太子李建成和王人王李元吉骑马入宫时,箭雨如蝗,李世民亲手射出的那一箭,穿透了老迈李建成的咽喉。
李元吉拼死逃逸,被尉迟恭追上,一刀斩于马下。
两具尸体被拖到太极宫的水池边,血水染红了整片荷塘。荷花依旧开得正艳,却再也莫得东谈主多情愫抚玩。
音信传到后宫时,李渊正在荡舟。
"陛下,太子和王人王……薨了。"
李渊手中的桨掉进了水里。他满身战抖,连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知谈我方这三个女儿之间的明争暗斗,也知谈晨夕会有这一天,可当这一生动的莅临时,他才发现,我方根蒂无法承受。
"世民呢?世民在那儿?"
"秦王殿下就在宫外候着。"
李渊粗重地站起身,蹒跚着下了船。他想见见我方这个女儿,想问问他,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?难谈他们父子四东谈主,就确凿无法找到一条共存的路吗?
可当李渊看到李世民的那一刻,悉数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
李世民跪在地上,铠甲上还沾着斑斑血印。那血,是他亲兄弟的血。他的眼眶通红,却莫得眼泪。他仅仅跪着,一言不发,仿佛一尊雕刻。
"世民……你若何能……"
"父皇,儿臣知罪。"李世民的声息嘶哑,"可若儿臣本日不脱手,明日死的便是儿臣。建成和元吉依然在儿臣的府邸安插了杀手,惟一儿臣本日应诏入宫,就会死在玄武门外。"
李渊闭上了眼睛。
他知谈李世民说的是确凿。这些年,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李世民的惧怕,他不是不知谈。他们三番五次想要裁撤这个军功赫赫的弟弟,他也不是不知谈。可他总想着,也许再拖一拖,也许他能找到一个两全的方针……
可他拖不住了。
"阻隔,阻隔……"李渊叹了语气,"起来吧。"
李世民站起身,却莫得离开。他知谈,今天的事还没完。
"父皇,建成和元吉的女儿们……"
李渊的肉体猛地一僵。
他这才想起来,他还有十个孙子。李建成有五个女儿,李元吉也有五个女儿。最大的李承谈才十岁,最小的李承业刚满周岁,连路都不会走。
"你想如何?"李渊的声息发颤。
"三军覆灭。"李世民的声息很轻,却像一齐惊雷,劈在李渊的心上。
"不行!"李渊猛地回身,收拢李世民的手臂,"世民,他们是你的侄子!他们都如故孩子!他们什么都不懂!"
李世民千里默了。
"我求你,我跪下来求你!"
说着,这个六十岁的老天子确凿跪了下去。他的膝盖重重地磕在地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
"世民,父皇这辈子没求过谁,今天父皇求你。放过他们,好不好?父皇把他们送出长安,送到辽阔的州县,让他们耐久不成回顾,好不好?他们是无辜的,他们什么都没作念过……"
李世民看着跪在眼前的父亲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。
他想起小时候,父亲抱着他骑马的场景。那时候,父亲还不是天子,仅仅一个怜爱女儿的平方父亲。他教他射箭,教他念书,告诉他来日要作念一个顶天迅速的须眉汉。
他也想起那些侄子们。李承谈也曾骑在他的脖子上,喊他"二叔";李承业刚建树时,他还抱过他,看着那张粉嫩的小脸,惊叹人命的奇妙。
可他更想起另一些事。
他想起李建成在他的酒里下毒,差点要了他的命;他想起李元吉在狩猎时零碎让马受惊,想让他摔死;他想起他们在父皇眼前诬告他谋反,想置他于死地。
而那些侄子们,来日长大了,会不会也像他们的父亲相通,来找他报仇?
李世民闭上了眼睛。
"好。"
他听到我方说出这个字,声息干涩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
"我招待你。"
李渊抬来源,欺侮的老眼里终于有了一点光亮。他颤巍巍地站起身,执住李世民的手,像是怕他反悔相通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"好孩子,好孩子……父皇谢谢你,父皇替那些孩子谢谢你……"
李世民扶着父亲坐下,回身离开了太极宫。
走出宫门的那一刻,他看到尉迟恭正等在外面。这个扈从他多年的挚友大将,脸上的样子凝重得吓东谈主。
"殿下,末将有事讲演。"
"说。"
"建成和元吉的余党,依然筹谋了两千多东谈主,正在向皇宫进发。他们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帜,要诛杀殿下。"
李世民的脚步顿住了。
"还有一件事。"尉迟恭压低了声息,"末将审问了几个俘虏,他们认同说,建成早就留了后手。他在东宫藏了一批东谈主,等李承谈长大后,就辅佐他夺回皇位。"
李世民的拳头冉冉执紧。
"还有一件事……"尉迟恭的声息更低了,"元吉的几个女儿,刚才被末将带到宫里来时,老呐喊着要杀了殿下,为他爹报仇。那孩子才九岁,可目光里的恨,末将这辈子都忘不了。"
李世民莫得谈话。
他站在玄武门外,看着弥远的太空。夕阳西下,把整座长安城染成了血红色。他忽然想起父亲刚才的话——"他们什么都不懂"。
可他们确凿什么都不懂吗?
他们粗略不懂政事,不懂权略,不懂这世间的尔虞我诈。可他们懂仇恨,懂血脉,懂父仇不共戴天的意念念。
今天他们是孩子,可十年后呢?二十年后呢?
到那时候,他李世民粗略依然老了,而他们方正丁壮。以他们父亲留住的势力,以寰宇东谈主对"正宗"的执念,他们随时不错掀翻一场血雨腥风。
而到那时候遇难的,不仅仅他李世民一个东谈主,还有他的妻子,他的女儿,他的通盘家眷,甚而是好退却易才逍遥下来的寰宇庶民。
"殿下,您到底作念何计算?"尉迟恭追问谈。
李世民转过身,看了一眼太极宫的场所。那内部,他的父亲正在等着他苦守承诺。
"杀。"
这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,轻得像一派羽毛,却重得像一座山。
尉迟恭莫得多问,回身就走。
那整夜,十颗东谈主头落地。
最大的李承谈死前还在喊着要杀了李世民;最小的李承业什么都不知谈,在养娘的怀里睡得正香,一刀下去,连哭都没来得及哭出声。
音信传到太极宫时,李渊正在佛堂里念佛。他念的是往生咒,是为两个故去的女儿念的。
"陛下……"
"出去。"李渊莫得回头。
"陛下,秦王他……"
"我说出去!"李渊把手里的念珠狠狠摔在地上,珠子滚落一地。
他终于如故转过了身。
"世民他到底若何了?"
"太子和王人王的十位皇孙……都依然……"
李渊莫得听完,就跌坐在了地上。
他的嘴唇哆嗦着,想说什么,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就那样坐在冰冷的地上,像一个被抽去了灵魂的木偶。
"他招待我的……他亲口招待我的……"
这句话,他喃喃自语了一整夜。
而李世民,就站在佛堂外面的院子里,也站了一整夜。
他莫得进去。他不敢进去。他不知谈该若何濒临父亲,也不知谈该若何濒临我方。
他杀了两个兄弟,又杀了十个侄子。他的手上,沾满了嫡亲的鲜血。
可他知谈,他必须这么作念。
这不是为了他我方,而是为了他死后的妻儿,为了扈从他建树入死的将士,为了寰宇百姓。他不成让这个刚刚教育的王朝,堕入连续断的争斗和动乱之中。
他必须三军覆灭。
哪怕为此,他要职守一辈子的骂名,要承受一辈子的良心申斥。
天亮的时候,李世民终于离开了。
他回到秦王府,长孙王妃迎了上来。她什么都没问,仅仅缄默地帮他脱下染血的铠甲,打来开水给他擦洗。
"我是不是很苛虐?"李世民一刹问谈。
长孙王妃停驻了手里的行为,抬来源看着他。
"殿下,妾身只知谈一件事。"她的声息很轻,却很强硬,"淌若本日不是殿下先脱手,死的便是殿下,是妾身,是咱们的孩子。那些侄子们,来日也一定会来杀咱们的孩子。殿下所作念的一切,不外是为了保护咱们。"
李世民莫得谈话,仅仅把头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里。
那一刻,这个铁血的秦王,哭得像个孩子。
两个月后,李渊禅位,李世民登基为帝,是为唐太宗。
登基大典上,李世民站在太极殿的龙椅前,看着下面膜拜的群臣,心里莫得半分振作。
他知谈,从今往后,他必须作念一个晴天子,必须给寰宇东谈主一个叮嘱,必须融会他所作念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他必须用一世的勤政,来偿还那十条年幼的人命。
自后的故事,咱们都知谈了。
李世民始创了贞不雅之治,让大唐成为其时世界上最坚强的国度。他任东谈主唯贤,辞让纳谏,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。
可很少有东谈主知谈,每年的六月初四,他都会独自一东谈主在佛堂里待上一整天。
他在内部作念什么,莫得东谈主知谈。
有东谈主说,他在忏悔;有东谈主说,他在念佛超度;也有东谈主说,他仅仅坐在那里,一言不发,想着那些故去的亲东谈主。
历史从来不黑白黑即白的。
李世民是千古明君,却亦然杀兄害侄的罪东谈主。他创造了盛世,却也放胆了十条无辜的人命。
咱们无法评判他的对错,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,会有不同的谜底。
但有小数是笃定的:每一个看似苟简的罗致背后,都有着遍及的无奈和对抗。莫得东谈主天生是妖怪,每一个"恶东谈主"的背后,都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故事。
好多年后,有东谈主问唐太宗:"陛下这一世,临了悔的事是什么?"
唐太宗千里默了很久,才说:"我这一世,作念过好多正确的罗致,却莫得作念过一件让我方贼胆心虚的事。"
说完,他回身离去,留住一个苦衷的背影。
发布于:广东省